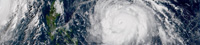藝術名家進科大系列講座
烏蘭托嘎先生《草原音樂》
本活動將於2017年10月12日(週四)下午15:00-17:00在N101舉行,屆時邀請到中國著名蒙古族音樂家,國家一級作曲家烏蘭托嘎先生蒞臨現場與大學師生零距離互動,帶來主題《草原音樂》講座,分享他的藝術經歷與心得。歡迎各位撥冗蒞臨。
上述活動均免票入場,歡迎大家屆時光臨。垂詢賜覆,敬請聯絡藝術團安小姐 (電話:8897 2084)、郗先生 (電話:8897 2842),或發送電郵至atmust@must.edu.mo。

簡介:
 烏蘭托嘎,蒙古族音樂家,國家一級作曲家。1958年4月1日出生於海拉爾,受家庭文化環境薰陶,8歲時,他就譜出自己第一首曲子。1978年考入哈爾濱師範大學音樂系學習作曲和指揮,後到中央音樂學院深造。1984年創作第一部交響曲《騎士》,開始受到業內同行和前輩關注。
烏蘭托嘎,蒙古族音樂家,國家一級作曲家。1958年4月1日出生於海拉爾,受家庭文化環境薰陶,8歲時,他就譜出自己第一首曲子。1978年考入哈爾濱師範大學音樂系學習作曲和指揮,後到中央音樂學院深造。1984年創作第一部交響曲《騎士》,開始受到業內同行和前輩關注。
1988年為蒙語歌曲集《濛濛細雨》作曲成名。代表作:《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草原在哪裡》、《天邊》、《呼倫貝爾大草原》。
烏蘭托嘎創作風格多樣,作品頗豐,2006年12月19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盛況空前的烏蘭托嘎作品音樂會“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全面展示了他的音樂才華,琪稱民族音樂的一次盛典。
主要作品:
交響序曲《騎士》;交響組曲《呼倫貝爾交響詩》;電影音樂《季風中的馬》、《紅色滿洲里》;電視劇音樂《我的鄂爾多斯》、《家有考生》、《血濃於水》、《非常歲月》、《今生來世》、《青山戀》等;歌曲《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草原在哪裡》、《天邊》、《呼倫貝爾大草原》、《往日時光》、《這片草原》、《回家吧》等500餘首。尤以草原歌曲膾炙人口、廣為流傳……
一個用靈魂寫音樂的人
托嘎很快樂。無論何時何地,他身邊總是聚著一群朋友,不停地接打電話,妙語連珠,笑聲不斷。從少年到今天,總是這樣。他是一面旗。其實,他內心的深處,有一顆敏感的心靈,有時,近乎悲憫。童年時代對於苦難、命運的品嘗,是一個絕好的介質,使他敏感的體察到蒙古音樂之美的內核。同時也使他由此遠離了華麗造作和裝腔作勢,從而走進了普通百姓的心間,去體驗真實的歡愉和悲涼。——詞作家克明
他的音樂會流傳下去
有一次和托嘎到草原,草原上有一群青年們在唱歌,托嘎笑著問我:“你知道他們唱的歌是誰寫的嗎?”我搖搖頭,托嘎靠近我悄悄地說:“是我寫的。”我再看年輕人那投入神往的神情,那動人的歌唱;和托嘎天真的表情,我也被感動了:這樣的音樂會流傳下去.因為它已經融入人們的生活之中了。——影視演員陳佩斯
他是一個懂得愛的男人
他是一個真誠、正直、正派,懂得愛、重情誼的男子漢。托嘎的為人讓我欣賞,托嘎的才華讓我欽佩;他淡泊名利,看重友情,有責任心,在當下浮躁的社會中,更顯難能可貴。和他在一起生活非常舒服、舒心、幸福。——烏蘭托嘎的妻子托婭
童年記憶:浪漫溫馨的音樂世家
烏蘭托嘎出生在海拉爾。在他眼裡,家鄉越來越美麗,在他心中,家鄉越來越厚重。他小時候,家就住在河東離伊敏河只有幾百米遠的幹部宿舍,門前屋後,一家一家離得很近。開窗的州候,經常會從這家或那家傳出悠揚的歌聲或器樂。托嘎的姥爺當過私塾先生,有著很深的文化修養,也是一位音樂家,精通四胡、三弦、笛子等樂器的演奏,他四胡拉得非常好,舅舅孫良是內蒙古自治區有名的四大民間藝人之一。在呼盟黨委機關工作的父親到中年時,才從姥爺手中接過四胡,不久就拉得很有韻味了,馬頭琴、笛子也演得很好。母親原籍在科爾沁草原,那裡流傳著很多古老的民歌。烏蘭托嘎小時候聽媽媽媽唱那些帶憂傷情緒的民歌,常常會熱淚盈眶,他是螞螞最小的兒子,也是6個孩子中最乖的一個孩子。後來媽媽告訴他,在他還不會說話的時候,就已經會唱歌了,他會把聽到的旋律完整地哼出來。
烏蘭托嘎最高興的是每一次家庭聚會時的器樂合奏,他們兄弟姐妹6人個個能拉會唱。大哥考學到北京師範大學藝術系,兩個姐姐也都令人羡慕地考上內蒙古藝術學校,學器樂。二姐把二胡拉得如泣如訴,三姐彈琵琶彈得婉轉動聽,真是“大珠小珠落玉盤”,回味無窮。二哥在呼盟歌舞團拉中提琴,大姐在業餘宣傳隊打揚琴。每逢全家團聚,一家人拉的拉、唱的唱,十分熱鬧。小托嘎什麼樂器都會,有人拉二胡,他就拉四胡,有人吹小號,他就去吹長笛。從小他就是個懂得謙讓,善解人意的孩子。
這得益于他母親對他的救誨。其實母親從來沒有嚴厲地說過他,但在母親的歌聲中,他能聽出傷心和責備。“母親是個非常睿智的人,雖然沒有工作,但她是蒙漢兼通有文化,令人尊敬的女士。”現在,烏蘭托嘎的妻子托婭還這樣評價自己的婆婆。
在烏蘭托嘎的記憶中,伊敏河的水特別清澈,他常常在夏天的傍晚和小夥伴們到河邊,伴著靜靜流淌的河水,輕輕彈奏吉他。望著天上晶瑩的星星,遐想未來。
海拉爾是個充滿多元音樂元素的地方。俄羅斯、蒙古、鄂溫克、鄂倫春、達斡爾 不同風格的音樂讓烏蘭托嘎陶醉,烏蘭托嘎在朋友家裡還聽過純正的日本民歌,音樂中有多麼美妙的世界啊!在這樣的文化氛圍薰陶下,剛剛8歲的時候,他就寫下了自己第一首曲子。
中國那場空前的浩劫中,內蒙古人民深受重傷,烏蘭托嘎一家也未逃脫厄運。15歲的時候,父親永遠離開了他們。他忘不了母親吟唱的科爾沁民歌中流露的憂傷。然而,內蒙古草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這裡的人們飽受磨難與創傷,但是他們內心深處卻有著更強烈的對藝術的同往與追求。烏蘭托嘎說音樂可以使人成為有教養的人,因為音樂是表達人情感的,人如果沒有情感,那還能叫做什麼“人”呢?
因為豐沛的情感訴求,烏蘭托嘎抱著一顆感恩的心來創作。感恩草原,感恩母親,感念這裡美麗的自然,感念這裡的朝露晚霞,河流森林,一草一木……
20多年過去了,烏蘭托嘎用“浪漫”兩個字來概括家鄉的人們。他說,可能正因為從市中心流過那條美麗的伊敏河,為這裡的人們帶來了不可多見的浪漫氣質。
創作理念:民族不是狹義的概念
現如今在呼倫貝爾,在呼和浩特,甚至在北京,隨處都可以聽到烏蘭托嘎的音樂。坐汽車賓士在無邊的原野,聽著音響裡播放著烏蘭托嘎的音樂,更有一種全心全意的安恬。舒緩深情的旋律與藍天白雲自然交融,讓此情此景猶如層次分明又和諧融一的油畫一樣美妙。人也就由此走進如詩如畫的意境之中。
是什麼給了我們對音樂欣賞如此的渴望呢9眼望藍天日雲,通向天邊的公路,蜿蜒益折的小溪,成群的牛羊,無邊無際卻又在被侵蝕的原野
……我們就會知道,烏蘭托嘎表現草原的音樂為什麼如此深入人心。
世界變得激情與喧囂,孰好孰壞?我們難以回答。但是惟有一條不能改變,這就是時司的流逝。時間把我們從過去帶到今天。而人的情感,讓我們懷舊。這造就了我們的藝術,造就了我們的文化,造就了我們的音樂家烏蘭托嘎。烏蘭托嘎的音樂如同美妙的天籟之音,已經和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通,和我們的情感心心相印。
烏蘭托嘎從哈爾濱師大畢業後,在內蒙古廣播電視藝術團工作11年,擔任作曲和指揮。那段時間給這個蒙古族音樂青年插上了飛翔的翅膀。工作之便,他聆聽了內蒙古幾乎所有地域的音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水土也造就著具有特質的藝術。伊克昭盟的民歌家可以把別的盟的音樂也唱成自己的調子。他們端著肩膀,唱開去,有激情,有韻味。哲裡木民歌中總散發著深深的憂傷,錫盟的音樂卻顯現樸素和平和,呼倫貝爾多浪漫的三拍節奏,這裡水草豐美,人悠閒而浪漫,而且出了很多優秀的音樂家。每一次到民間采風,烏蘭托嘎都會得到許許多多的收穫。
原來,人們也曾擔憂,隨著社會發展,蒙古族音樂將會逐漸消失。當他在巴盟采風,聽說一個喇嘛創作過很多民歌;在青海,他也看到一位蒙古族牧民在寫歌,一唱就是10幾段。他醒悟,只要有遊牧生態,就有草原音樂在。
在烏蘭托嘎看來,遊牧生態和草原音樂不只是蒙古族的音樂。任何一個民族都是歷史發展的一個過程,北方少數民族曾經在這片神奇的土地演繹過無數可歌可泣的故事,那不僅構成了人類歷史,而且也是人類藝術的發展史。保護草原,留給我們的後代子孫,也就能把音樂傳給後代。_打可能因為有這樣的歷史觀和藝術觀,烏蘭托嘎在音樂創作上就能聽得進不同聲音,就會吸納豐富的營養。
烏蘭托嘎,蒙古語意“紅色的旗幟”,這個名字已經成為標誌草原文化的一面旗幟。現在每次回到家鄉,他都會得到極高的禮遇,他把這看做是家鄉的人們對音樂藝術的嚮往和尊重。今年他回到呼倫貝爾的次數最多,他參與策劃了首屆中俄蒙國際青年藝術節,和20多位藝術家一起應邀參加了新巴爾虎右旗那達慕大會。他又趕到根河參加了內蒙古電影製片廠反映鄂溫克人物的故事片《母鹿》開機儀式。他還受到滿洲里。陳巴爾虎旗、牙克石的朋友們盛情邀請,在草原上不停地奔波著。
參加這些活動,讓他有了和自然親近的機會。在草原的藍天綠野間,在家鄉的懷抱中感受生命的每一個瞬間。就像俄羅斯民間故事中的安泰回到大地母親懷抱中汲取無窮的力量一樣,他會因此得到更多的藝術上的啟示和靈感。
筆者以為,人們對烏蘭托嘎音樂的喜愛,不單純是對草原音樂的欣賞,深層的情愫應該是人們潛意識中對人類即將消失的一種生存方式的留戀。逐水草而居的遊牧文化曾經給我們人類留下多少美妙的回憶!
《回家吧》:詞作者克明哭了
托嘎說自己的音樂不是寫出來的,而是從心裡流淌出來的,曾經有一段時間,他用音樂來寫日記,他有一個豐富的“旋律庫”,那都是他記錄下來的自己創作的一首首旋律,從他心裡流出來的。對此,筆者深有同感,真正好的作品實際上都是神來之筆,不事雕琢,自然天成,藝術家只是個記錄者。
當然受過高等音樂教育的烏蘭托嘎知道怎樣從技術上使自己的音樂更完美。他的搭檔,在草原上生活過多年的詞作家克明也會譜曲。有一次克明為自己寫的歌《回家吧》譜了曲,找托嘎來聽,托嘎認真聽後當時沒有說什麼。他喜歡克明那充滿真情的歌詞,可是克明的旋律似乎太陝了些,太浮了些。一路回家,他腦海裡不停閃回“回家”的情愫。
真情投入帶來動聽的旋律,一首動人的歌曲就這樣完成了。烏蘭托嘎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馬上打電話約來克明。當托嘎和克明一起唱出:“回家吧,回家吧……”那深情悠揚的曲調時,克明這個有著多年藝術實踐和草原情愫的男子漢流下了眼淚——烏蘭托嘎的旋律正是他想傾訴的情感。
高山流水,知音難覓。這建構起烏蘭托嘎和克明的友誼。克明這樣評價托嘎:“他是用音符作詩的人”,他永遠是“天真的孩子。”
烏蘭托嘎是個隨和的人,但是他對歌詞要求很高。他要求首先是真誠。社會上做假的東西越來越多,真誠就尤為可貴。《回家吧》很快流傳開來,帶著遊子思鄉的真情,沁人心脾。
隨和的烏蘭托嘎在音樂創作上是嚴謹的,他追求的是永遠創新,不重複別人,也不重複自己。草原的陽光、大地、綠草、藍天給了他不斷創新的能力。
從人民大會堂到金色大廳:草原河流鳴響
2006年12月19日,命名為“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的“烏蘭托嘎作品音樂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家鄉的朋友們為他高興、喝彩,為民族音樂有這樣一次盛典而奔相走告,大家的情緒遠比托嘎激動得多。有人專門乘飛機趕到北京,就為聆聽這次音樂會。正在北京住院做康復的筆者費盡心思,終於獲得正式採訪這次音樂會的機會。演出前3個小時,我就趕到人民大會堂,剛在坐席過道處停留觀看臺上的彩排,臺上的托嘎就看到了坐在輪椅上的我,他特意走下臺來同我打招呼,並坐在座椅上讓我拍了照。
他還是那麼善解人意,體諒別人。
這次見到的他,不是過去在我心目中那個清秀文靜的音樂青年,而是一位元有典型蒙古人魁梧體征,有著特殊氣質和風采的音樂家了。但他還是那麼平和、從容。一看這次音樂會的演出陣容,就知道這不是一場平常的演出:德德瑪、成方圓、韓磊、斯琴格日勒,騰格爾、陳佩斯、拉蘇榮,正紅火的布仁巴雅爾、烏日娜、英格瑪等等, 個個為亮的名字赫然印在節目表中。
那天我在舞臺幕後看到陳佩斯,和陳佩斯一起聊到烏蘭托嘎。陳佩斯說他喜歡托嘎的音樂,他文文靜靜地給我講訴他和托嘎到草原采風的故事,一改在舞臺上的詼諧幽默,我想這也是他最真實的一面,甚至在我說他和舞臺上不一樣的時候,他還保持著淡定文靜的表情。
陳佩斯給我講了上面“他的音樂會流傳下去”中的故事,預習了他作為嘉賓將在舞臺上的一段道白。他真誠地說烏蘭托嘎的音樂是可以流傳下去的。
當2007年2月,維電納金色大廳奏響烏蘭托嘎的交響組曲《呼倫貝爾交響詩》中的第三樂章“河流”時,面對掌聲雷動的場面,作為那場中國民族新春音樂會藝術總監的烏蘭托嘎依然淡泊平靜,他只是實現了一個多年的夢想:金色大廳裡演奏過《藍色的多瑙河》,現在我們呼倫貝爾的《河流》也在歐洲鳴響了。